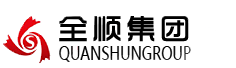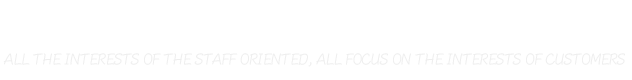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人成长起来,真正为咱农民工做事
发布者:admin 发布日期:2010-01-17 03:35:00 浏览量:
A:“我是摸着石头过河,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创新!”
在张全收的老家,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,他的名字几乎是无人不知。
今年39岁的他,卖过爆米花,做过油漆员,还做得一手好馒头,很多人现在还喜欢称他“馍老板”。在深圳把事业做起来后,他积极支持家乡的慈善事业,捐钱盖希望小学、敬老院,这都是当地人耳熟能详的事情。而真正使他为人们所熟知的,还是他在河南和深圳两地创办的“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”。
大家要出去打工时,总会有老乡告诉说:“深圳有个张老板,对工人很好,没活干的时候也有工钱拿。”
就这样一传十,十传百,大家都纷纷来到深圳张全收的公司,现在他企业的农民工已经达到1.3万人,有70%左右都来自河南。说是人力资源开发,可能用“劳务派遣”这个词更易理解。全顺公司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,哪个厂要人,就“打包”调人过去,这个厂干完了,就调到另外一个厂。碰到没活的时候,工人们就呆在总公司的培训基地里,吃住免费,而且每天还有35元补助。
在珠三角地区,企业用人有很强的季节性。遇到淡季,便大量裁减工人;一旦接到订单,又难以在短时间内招到充足的员工。“但是通过张全收的公司,企业在用人上就要灵活很多,而且全顺的员工从来不惹麻烦,管理起来也很省心。”因为这个缘故,和全顺公司合作的企业都愿意支付给其一定的管理费。
张全收赚的就是这部分管理费。
近年来,在全国各地愈演愈烈的“民工荒”,为张全收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,但是在珠三角这样一个劳动力输入大区域,“劳务派遣”的市场发展并不算繁荣。据有关资料统计,当地真正从事过或在提供“劳务派遣”服务的公司大概有40家左右,但其中已派遣人数真正在“千人”以上的公司估计不到20家。能达到全顺如此规模的更是少之又少。
“现在做我这一行,能做到我这个规模的不多。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,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,但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创新!”张全收有些骄傲地说:“第一,你得有人缘关系,他得信任你的运作模式;第二个,你作为一个老板,得要真诚,在人家面前说的每一句话,宁愿亏也得算数。第三个主要是对客户要有耐心。工人的工资、安全、生活标准等十几项内容都要一项项去谈啊,否则工人的利益怎么保证?”
B:“全顺公司把农民工组织起来,起到类似工会的作用。”
这个世界上,最难管理的就是人。而对于张全收来说,他不只是这1.3万名农民工的管理者,也是他们权益的保护者。如何把握好这两者的平衡,考验着张全收的智慧和耐力。
他爱絮叨:“要时刻注意,安全第一。进车间不要乱动机器,晚上回宿舍睡觉要看路。过马路两边看,要走人行横道线。”
他爱管闲事:“你们有些男孩子,耳朵根子打了一圈的耳洞,头发留得比女孩子还长,像什么话,以后统统留短发,不要整得跟个小流氓似的!”
张全收是个心直口快的人,说多了,管多了,自然会有人有意见。这也包括社会上的一些非议。
在全顺公司,大部分工人们的工资都是留下每月300元的生活费,其余寄回家里。记者在张全收的公司里看到了一大箱子的汇款单,“这都是农民工们为家乡做的贡献啊!”张全收对记者说。
张全收从打工仔做起,吃过苦,知道打工者的不易,更知道每一个出来打工人的身后都有一个沉甸甸的家庭。“我向人家的父母保证过,一家两个孩子跟着我,一年寄回去两万元,保证五年盖新房;有的一家在这干,两年就能住新屋。”
对于张全收的这种做法,有人提出“是在克扣工人工资”的质疑,张全收对此忿忿不平:“1.3万的人跟着我干,谁敢克扣试试。我如果这么干,这些工人早跑光了。”
“有1.3万人跟着我干”是他面对一切质疑最强有力的信心保证。所以,他也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保障工人的利益上。张全收的公司总共分为四级;张全收、副总、各厂主管和小组长。如果员工们遇到权益被侵害的事件,不仅可以向主管和小组长反映,也可以直接告诉张全收。
“如果发现有工厂苛刻地对待全顺员工,我们便出面交涉。若全顺员工和所在厂工人之间发生冲突,我们就要求双方管理人员协商解决或者提交派出所来解决。要是我们的员工不能得到公平对待,我们就撤回所有工人。”张全收说,“一个人,你想把人家赶走就赶出去了。可是现在,我会告诉这些企业———
还有他们的老板在啊。”对此,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教授于建嵘评价说:“这方面全顺公司起到了一种类似工会的作用。张全收做到了许多连政府都没有做到的事情。”
C:“不管别人怎么说,至少农民工是认可他的!”
有人这样评价张全收:“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老板,他懂得如何与合作企业谈判,为全顺的员工争取到充足的保障,同时也为自己获取更大的利润;他也是一个实在的好人,当他的员工在制度的渠道内不能获得有效的权益保障时,他就结结实实地把所有也许并不属于他的责任肩负了起来。”
在全顺公司,员工无论是工伤、意外伤害还是重大疾病都实行公司全面管理负责制,员工不用掏一分钱费用。
一次,有一个工人阑尾炎穿孔,张全收派人把他送到医院去,医药费用全部由公司出,还从老家把他的父亲请来照顾他。结果没住几天医院,这父亲半夜却带着孩子从医院跑出去了。
一听这事张全收就急了,看病花了将近一万块钱,他知道老人家是怕出钱,又火急火燎地派人把他们找回来了:“这里小病公司看、大病送医院的制度知道吧?跑啥子跑,万一口子长不住,肚子破了怎么办?”
这样的故事还很多,平舆打工妹李娜(化名)晒衣服时摔伤脊椎,张全收送她去看病,替她出了5万多元的医药费;郸城小伙刘龙乾逛街时被打劫身中四刀,张全收几次送去1万多元的医药费……“哪些是应该担负的责任,哪些不是,这很难说得清楚。一个员工出去玩掉到河里淹死了,我给他家里拿了3万元,他父母从农村跑来,头磕得咚咚响,这些都是情份啊!”
张全收的手机里,存着很多员工们给他的短信,有表示感谢的,有给企业发展提意见的:“老板爸爸,你好!春节愉快!”张全收拿给记者看,笑着说:“他们都叫我‘爸爸’,我有那么老吗?其实,因为你对他好,他才对你好。”
张全收对员工究竟怎么样,光听他说是不行的。在调研中,于建嵘和他的同事们都是自由出入全顺的合作企业,常常随手就“抓”来一个农民工,和他攀谈起来。几个月来,调研组走访了全顺几百名员工,结果只有一个人说张全收不好。
调研组一直在问工人一个问题:“假如张全收对你不好,克扣你的工资了,怎么办?”得到的答复常常都是“不可能”,他们一再逼问“假如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呢?”工人回答说,“那我就去劳动局告他。实在不行我就不跟他干了!”
而事实上,深圳市当地的劳动管理部门还尚未接到工人对张全收的投诉。而全顺公司的员工队伍也愈来愈庞大。
“不管社会、政府、媒体是如何评价张全收,我们感受很深的一点是,这些农民工是认可他的!”于建嵘说:“这也正是我们把特别奖颁给他最大的原因。”
D:张全收很困惑,这个事业究竟可以做多大?
这个奖项,让张全收认识了很多“三农”学界的专家,他常常会问他们:“你说,我这个事业究竟可以做多大?”
虽然在他的家乡河南他获得了足够的荣誉,虽然此次他所创新的“农民工权益保护模式”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,可是对于未来,他依然困惑。
“按理说我应该会发展很大的。首先企业有需求,再者也有很多的农民要出来做工。明年有可能我会组织转移3至5万人的规模,但是说实在话,这些我现在想都不敢想啊!”
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已经数年有余,分别在河南和深圳两地挂牌办公。按照国家的规定,所有涉及到劳务租赁业务的公司必须得到劳动部门的批准,才能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。河南的公司手续很早就办下来了,但是在深圳,张全收却一直无法得到劳动部门的认可,后来好不容易才在深圳市工商部门登记注册。
记者在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劳动站采访时,其劳动稽查大队的一位负责人承认:“张全收的公司,为当地企业解决了用工短缺的问题,也通过有效手段保护了农民工的权益。”“但是如果张全收的合作企业拖欠工人工资跑了,全顺公司就会给当地劳动部门施加压力。”以前,也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
在当前劳资关系并不稳定的背景下,作为劳动主管部门,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和担忧是很正常的。“最根本原因是,这种公司制度下的组织化,即使因为组织者个人的道德力量可以在正常轨道中行走,却依然被定义为边缘化的存在,无法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。”于建嵘说。
而深圳,在其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,正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出去,进一步引进高新技术产业。“这其中,全顺公司的工人显然还是属于这一范畴,文化水平普遍较低,正是深圳市在发展中欲淘汰的对象。”张全收对此相当了解,但他并不担心,因为他的工人不仅仅在深圳和珠三角,现在他的工人在粤北的河源,甚至福建、江西都有。“产业转移也是大势所趋,但这类工厂到哪里都需要工人,我的工人可以随着工厂走,对工人来说到哪里都是打工挣钱!只要他有饭吃,有钱挣,还是愿意跟着我干的!”
现在张全收最关心的是,从明年一月一日起,《劳动合同法》即将实施,对于劳务派遣也出台了一些新的规定,这必将会给全顺公司的发展带来一些冲击。他现在每天都在考虑如何与《劳动合同法》接轨的问题,希望自己在深圳的公司早日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。如果得不到认可,公司想进一步做强做大是不可能的事。
“第一个吃螃蟹的,路总是会走的比别人艰难。”张全收说,自己经过这几年的闯荡,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,吃了多少苦,受了多少累,只有自己心里清楚风光背后的辛酸和无奈。
“我曾经想过,以我现在的经济实力,这个公司不干了,到外面去搞点别的,要赚钱也不是很难的事。但是又很担心这些工人,跟着我这么多年了,现在他们都这么信任我,如果我不干了,他们怎么办?”
张全收的疑惑,看来绝不是哪一个奖项或者哪一批人可以清楚回答了的……
下一篇:深圳打工的领路人